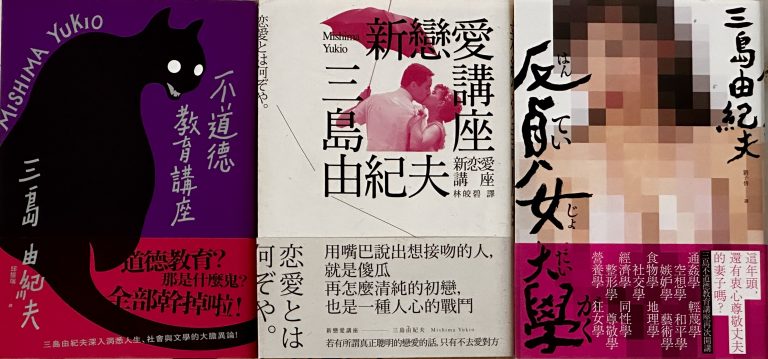大家所熟知的三岛是文学的三岛,细腻的文字背后是某种暴烈,像喷瓜一样从瓜瓤中喷出自己的种子。而作为导演的三岛,他的电影延续了他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视觉与思想上的暴烈在影像上完成了统一。三岛唯一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是1966年完成的《忧国》,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忧国》的设定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2月28日,二二六事件后的第三天,讲述了一名皇道派的大尉因为政变失败而与妻子切腹自尽的故事。《忧国》能视为三岛再一次的切腹预演(在这之前是他和细江英公合作的写真集《蔷薇刑》),他把他的人生浓缩在这篇短篇小说里,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忧国》并不是唯一一部谈及二二六事件的的电影。1954年佐分利信(曾出演小津安二郎的《彼岸花》《户田家兄妹》)就指导了《叛乱》,该片改编自立野信之的直木奖同名小说。在三岛的《忧国》之后,日本新浪潮导演吉田喜重也在1973年推出了《戒严令》,是他的日本激进主义三部曲(其他两部为1969年的《情欲与虐杀》和1970年的《英雄炼狱》)中的第三部,该片从涉及二二六事件的哲学家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推动者北一辉切入,回溯了北一辉和当时受他影响的激进青年之间的关系。以执导江户时代剑豪电影闻名的五杜英雄也曾于1989年执导“226”,荻原健一、三浦友和与竹中直人主演,谈及了226事件的始末。在这些电影当中,吉田喜重的《戒严令》似乎与三岛的《忧国》有重叠之处。
回看三岛的电影与他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观众或读者所看见的不仅仅是他的自杀预演,但同时也是他的美学理念的表达。三岛的作品中似乎都保有某种一致性,不仅仅是他的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美的阐述。《忧国》从小说到电影的转换像是三岛为这个故事赋予一个肉身,让他的意识附身在这部消失已久的电影里。这篇影评不仅要剖析《忧国》的媒介转换,同时也要为这部电影在日本电影发展史锚定一个坐标,从两种不同的面向去解读三岛与他的作品。
《忧国》的媒介转换
三岛的小说《忧国》对于二二六事件的描述侧重内心的描写,也着重描绘了切腹的细节,也涉及了一些情欲的描写。如果仔细对照电影和原著,小说中的视觉与心理描写都在电影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刻画,小说和电影两种媒介被三岛完美的转换。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楼下佛坛上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御照和皇太神宫的牌位供在一起。每天早上出勤之前,中尉偕妻子跪在佛坛下边深深垂首而拜……这个世界一切都有严肃的神威加以保护,而且浑身都充溢着震颤的快乐。”这样的一个段落在电影中被浓缩成一段蒙太奇里的一个镜头呈现。在这个镜头中,中尉以及妻子对着皇居鞠躬膜拜,妻子的闭着眼的脸部特写和皇居的影像重叠,似乎浑身都充溢着震颤的快乐一般。电影《忧国》里诸如此类的表现蒙太奇俯拾皆是,这样的影像表现有稍显刻意的感觉,让人不禁想起以前苏联时期的蒙太奇电影。这也让电影变得更加像是立场的表述,但这也似乎是三岛所要达成的意图之一,这种过于古典的表现形式把他的作品和同时期的新浪潮电影区隔开来。

能剧舞台的设置,让切腹成为一场近乎仪式般的表演。(来源:电影截图)
三岛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时选择以能乐剧场的形式呈现,这让中尉和妻子丽子的切腹更加像是一场展演。三岛对于能剧的迷恋在他十三岁那年被外祖母带去看能剧时就开始了,他在之后更说“能剧一直是我的文学作品中的一股暗流。”[1]能剧的形式感和仪式感赋予了小说缺乏的表演性,让观众更直观地看见行动/仪式本身,让电影更富戏剧感。三岛深知影像和文字的差距,因此在影像上更侧重于行动本身,而小说中则是为故事加深了心理上的深度。能剧的舞台也让三岛有机会去探索不同的构图,把他对于死亡的迷恋提纯,让两人的死更趋近一种仪式。能剧的形式不仅是对古典的回归,更是三岛思想的具象化。他在电影中完成了对死亡的仪式化演绎,而四年后,他用生命验证了行动的绝对性。他自己出演中尉一角,正是最直接的宣言——真正的信仰必须通过行动去践行,哪怕是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如果说能剧的形式赋予了《忧国》这个故事仪式感或舞台感,那电影作为另一种形式则是提供了节奏感。电影《忧国》将默剧与能剧结合,唯一能说话的是电影的节奏。电影的节奏掌控松弛有度,搭配华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第三幕〈爱之死〉,完成了文本之间的指涉[2]同时也赋予了节奏感。电影的前半部分在节奏上稍为缓慢,为后面快节奏的高潮做了铺垫。在中间的段落,丽子与中尉在切腹前缠绵的场景不断聚焦于身体的特写。他们不为他们即将面对的死亡哀伤,而是用官能性的快感去庆祝这场死亡的飨宴。
对于丽子和中尉甚至是三岛本人来说,死亡不是肉体的终结,而是某种意识的流动。正如《春雪》里昭披耶王子所说的:“尽管肉体没有连续,只有妄念是连续着的话,把它们当作是同样的个体来想也未尝不可。如果不说个体而叫做‘一种生命的流动’也许更合适吧。”这种生命的流动具像化到电影中则是以大量的特写和较为快速的剪辑来表现。电影把小说中官能性的体验以更直白的影像形式转化为视觉冲击,也回归到三岛作品的母题,即肉欲与死亡的交织。
电影《忧国》与日本新浪潮
回观电影完成的60年代,当时的日本电影新浪潮正兴,许多电影的题材都离不开爱与死的主题,这与三岛作品的母题也几乎重叠。吉田喜重的《戒严令》结合了真实与虚构,围绕着爱与死的主题展开,建构了一个“可用的过去”(大卫·德瑟语)。
三岛的电影虽然不能算是新浪潮的电影,但是他的影子却也不断出现在许多新浪潮的电影中。吉田喜重的《戒严令》在政治立场上和三岛是在光谱的两端,但是却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岛谈及《忧国》时说过这篇小说建立在巴塔耶那本把死亡和情色联系在一起的著作《色情史》上,“日本人的色情中,往往伴随着死亡,那么在被政治和正义逼迫之时,在必须为了政治殉道的时候,色情又会以什么样的最高形态被呈现呢?我想探索的就是这个。”吉田的《戒严令》似乎不经意回应了这个问题,北一辉在电影里的受虐倾向以及对天皇犹如疯魔般的幻想。两种不一样的色情,两种不一样的解读。
《忧国》虽然曾在日本艺术影院行会(Art Theatre Guild,简称ATG)短暂上映过,但这部电影不属于日本新浪潮电影。虽然如此,这部电影和同时代的新浪潮电影形成了对话的关系,也表现了战后青年的迷茫状态。三岛和吉田两人的电影都在思考信仰、死亡、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构一个可用的过去来思考过去之于现在的价值。《忧国》的电影化,不仅是三岛个人信仰的影像化展现,也标志着日本电影在形式与思想上的一次重要尝试。这部消失已久的电影,至今仍然折射出那个时代未解的命题。
在三岛诞生的100年后重看《忧国》,再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已然褪色,剩下的是死亡与爱欲的纠缠。试图从这部电影去解读三岛自戕的心理状态或许是徒劳的,但它所映照的时代命题,至今仍未得到答案。在分崩离析的世界,寄居在那个被燃烧殆尽的金阁,看时代的潮起潮落。
[1] 见《近代能乐集》中,玖羽所写的〈作品题解〉中对三岛《日本的古典与我》的引用。
[2] 关于电影《忧国》与华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互文性,可参考王淑容的《〈爱之死〉的构图:三岛由纪夫的〈忧国〉、电影《忧国》与华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